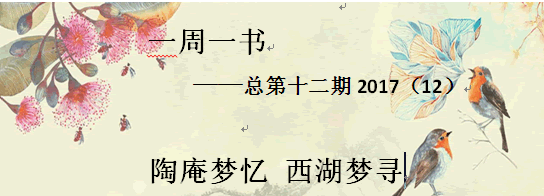
文献建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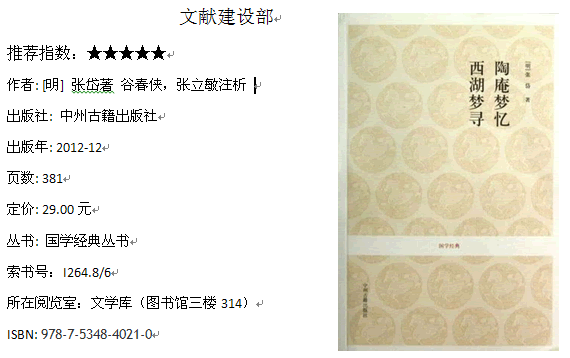
张岱,一名维城,字宗子,号石公、陶庵、蝶庵、天孙、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故又自称“蜀人”、“古剑”。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年诸说不一,据商盘《越风》张岱小传推算,当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享年九十三岁。
《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是明末张岱的两部笔记小品著作, 记录了明末江浙一带的世态人情、风俗生活, 表现了作者对于旧王朝的眷恋和对明清之际传统风俗文化变迁的浩叹。本书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主, 参考他本, 加以注释, 并有简要的赏析, 以期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赏读。
山阴张岱出生在显赫之家,上辈皆是高官名士,他年幼时即有才名,据说张岱八岁时祖父带他去西湖玩,迎面撞见了不起的名士陈继儒跨鹿而来,眉公早就听说张岱才具非凡,正要考他,指着纸屏上的一幅画《李白骑鲸图》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小张岱甩了甩脑袋就说:“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陈继儒笑到不行,说:“何等敏慧,是吾小友也。”张岱已天纵其才,且挟富贵优裕,注定是名动一时,慷慨任侠风流才子。
张岱的小品文又颇有“高级小资”的味道。他的生活是充满贵族文人情趣的:舞文弄墨、莳花弄草、松风听雪、春水煎茶,处处体现着晚明士子的风流,却又超越了一般的风花雪月而蕴含了无尽的人生哲理(尤其是结尾)。在《目莲戏》中作者写本家季叔排演目莲戏之事,台上戏子“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觔斗蜻蜓、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窜”,而台下观众“万余人齐声呐喊”,热闹的程度甚至使当地守官以为“海寇卒至”,其万人空巷摩肩接踵的程度可见一斑,然而写到这里作者笔锋一转,“一曰果证幽明,看善善恶恶随形答响,到底来那个能逃?道通昼夜,任生生死死换姓移名,下场去此人还在。”又说“装神扮鬼,愚蠢的心下惊慌,怕当真也是如此。成佛作祖,聪明人眼底忽略,临了时还待怎生?”正所谓境由心造,戏如人生,一股看破生死的豁达与洒脱之气扑面而来,升华了全文,堪称点睛之笔。
张岱是一个钟情于梦的人,早年的他过着钟鸣鼎食的纨绔生活,而在一瞬间国家覆灭了,他径直跌落到赤贫的人间底层:“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如野人”。然而愈是现实困顿,愈是眷恋着旧日的繁华不肯罢手,虽然作者也曾将其归因于早年生活的奢靡和对生命的浪费:“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然而“繁华靡丽,过眼皆空”,留在心头的只有回忆。追忆似水年华使往昔种种的罪孽释然,而今日的处境是如此的可悲可叹。对于张岱而言,他是在回忆中把现实和梦境叠加在一起,他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他心目中的世界,而他又在这个真实与虚幻交错的世界中回忆往昔。他想告诉人们,即使天翻地覆改朝换代,即使国破家亡零落人间,我还有回忆,我还有梦。在回溯梦的过程中,我的生命和人生有了一个新的展开与延续,故而今日生活的沦落恰恰反衬着昔日的荣华富贵,没有了今日那么回忆的重量也无从说起。那么自己的人生也许和任何一个虚掷光阴的纨绔子弟没有任何区别吧。
张岱和他笔下的人们一起见证了末世的最后一场繁华,然后剧终人散,落得一场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正如在《金山夜戏》中所记载的那样,张岱因见“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于是一时兴起,命人“盛张灯火大殿中”,自己则“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最后“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