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壹学者
杨震,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长江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杰出的化学家。

今天推荐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杨震的口述文章。这是一个癌症药物新星从生死线上归来坚持追梦的故事。
杨震的童年是孤独的,因父母被批斗,从小受人欺负。1990年代初,杨震在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完成了天然紫杉醇的首次人工全合成,轰动世界。正当意气风发之时,杨震在一次实验爆炸中重度烧伤。死里逃生,他对生命做了三个承诺:不做坏事、同情、尊重宗教。2001年,杨震回到中国,参与建设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孤独是种力量
和大多数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一样,我童年的记忆多是难以忘却的孤独。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时代,作为家里第七个孩子,我的出生并没有收获什么祝福。母亲很疼我,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也都疼我,但是深深的孤独感从未离开过我。小时候的我性格孤僻,常常一个人出门转,所以常常走丢。哥哥姐姐对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一个小脑袋从门后面探出来,怯生生地观察外面的世界。后来我养成了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跟自己娱乐、自己做玩具,什么都是自己的习惯,这整个经历和过程养成了我独自思考的习惯。因为出去玩也好,自己玩也好,我总是自己问自己一些东西,后来我知道这恰恰是思想升华的时候。

我是在沈阳出生的,七岁的时候全家下乡了。爸爸是留日归来的学者,日伪时期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石桥子中学任教,这段历史后来成了我们全家的痛。由于爸爸当时会说日语,他负责的学校又帮助日本人种粮食,因此,在“文革”期间爸爸吃尽了苦头。
1971年,我们全家从沈阳被遣送回爸爸当初做老师的凤城县。那时候,爸爸经常被批斗。头一天批判他,第二天就批判我,因为批判他的时候我没参加。我不能参加啊!那很惨的!就跟现在看的很多片儿一样,挂着大牌子,揪着头发,戴着砖,我没法看那个画面,所以就跑了。第二天学校就把我揪出来,然后批判我,说我是改造不好的人的子女。
我小时候上学很艰难的,人家走大路,我只能爬山路,因为我要走大路的话就得给买路钱,我要不给,他们就打我。当时我母亲还有些零钱给我,一般她给我五分钱,希望我中午可以买点吃的,但那些钱我很少花,基本上都是买路了。走到那儿把钱给他们,今天就不挨揍,我要是没钱,就不能走那条道。为了躲他们,我习惯走另一条道,真的很恐怖的,狼啊什么的野兽都有。但我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后来养成了一个挑战权威、仇视优越感的习惯。正因为我从小受到弱势群体的待遇,我一直同情弱者。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弱不一定是软弱,只是人生的一个经历过程,这个感悟对我一生都很重要。一般来讲,我跟任何人相处,只要他不欺负人,我们都是好朋友,一旦他出现欺负人的时候,就碰到我的底线了。慢慢养成的这种独立、刚强、不怕苦的性格,对我整个化学研究生涯有很大的帮助。
单纯专注就好
我是药学院的学生,化学基础并不太好,有机会师从香港中文大学黄乃正院士,我真的很幸运。那时候年轻的我对世界充满好奇,也从来不计较多干活,在实验室里,我愿意帮助任何人做实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像个神童,搞定越来越多的实验,连黄教授也非常吃惊。当时我身体很棒,喜欢打网球,打球的对手是曾经参加香港公开赛的香港中文大学冠军,我俩每天早晨晨练。我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但是大家都夸我网球水平进步很快,体力好,技术也不错。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日子过得飞快,成长得也飞快,收获很多,真的很幸福。
当黄教授推荐我到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追随当时合成化学界的一代宗师尼克劳(Nicolaou)教授读博士后时,我并没有太多伟大的理想。当时我和太太说,就想去赚两万美金,然后我就回来。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概念。我是跟着我的实验来睡觉的,就是它几点结束了,我就几点醒。那时候我的生活简单得一塌糊涂,人家买车我不买,我骑自行车,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另一方面省钱。我自己因为是穷孩子,什么都会做。我做饭很好吃,自己带饭很省钱,基本上一个星期花不了多少钱。人家到美国先去学习英文,我哪儿也不去,天天在实验室干活。后来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学英文,我说,在美国说英文有用吗?那时候我还有很多小时候的心理阴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奴隶。我一心一意想着两件事:第一是别被老板提前炒鱿鱼,第二是挣完两万美金我就回家。

那时在实验室里,任何人需要帮忙都愿意找我,我无代价地给他们干活,帮他们备料,做各种各样的反应。我当时在想,我时间不多,必须要学到我希望学到的东西。怎么学?跟人家讲“你教我”?这样是不会有人教我的。那怎么办?“我帮你干活啊!”这个是最有效的,因为他要想让你干活,他必须把真的东西告诉你,否则你把它就给做坏了,这个时候你学到的知识就全是真正的好知识。
我刚到美国时和导师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第一天去研究所见导师时,他搂着我脖子,很亲切,随后的两个月,他就再也不理我了。我问周围的同事:“教授咋不跟我说话呢?”同事告诉我,等我做出东西来,教授才会理我。我后来理解此“冷处理”是教授的一种特殊管理方式,并且逐渐接受这种会让人去思考的方式。但在当时,刚到异国他乡的我觉得很受伤,所以,我在实验室有些古怪的行为。比如:实验室经常拍照片,我从来不参加。因为我觉得既然你不喜欢我,我就不跟你照相。好几次实验室的秘书都跟我说:今天又照相,你能不能不走?我还是溜走了。回想起来,青年时代的我幼稚而倔强,所以今天我也可以理解年轻人,哪怕有些小古怪也没关系,我也无条件地爱他们。

世界的新星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曾经有两个诺言:一个是关于登月的阿波罗计划,另一个是征服肿瘤。这两个科学诺言当时震惊世界。阿波罗登月70年代初就实现了,但征服肿瘤一直遥遥无期。人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来的二倍体生物个体,称为二倍体。细胞的复制过程遵循2、4、8、16……法则,可用2n表示。细胞复制过程涉及一种叫微管蛋白的关键物质,简单来说,微管蛋白在细胞中的功能就像房屋中的砖块,细胞的复制是将这些“砖块”有序地重组,构建成两个独立的细胞。人体正常细胞的复制过程可控,而肿瘤细胞则是一类“细胞复制”无法控制的癌变细胞。从细胞复制的角度来讲,如果能够阻止“砖块”的解聚,是不是就影响房间的分化?如果找到外来物种能有效地抑制“肿瘤细胞的复制”机制,不让这类“砖块”解聚,那事实上我们就可以抑制肿瘤的扩散了。然后再通过其他的化学手段、治疗手段,就可以抑制或治愈肿瘤了。
1962年,美国植物学家巴克莱(Arthur S. Barclay)采集了加州杉树(Pacific yew, Taxus Brevifolia)的树皮。1964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沃尔(Monroe E. Wall)和瓦尼(Mansukh C. Wani)教授从树皮中分离得到具有抗肿瘤活性的紫杉醇。1971年经X光衍射分析确定了紫杉醇的结构。但由于它的溶解度不好和分离上的困难,他们没有继续研究该物质,并将它放到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化合物库里。1979年,美国纽约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的霍维茨(Susan B. Horwitz)教授发现紫杉醇是通过抑制微管蛋白的解聚实现它的抗肿瘤效果。从机制上来讲,紫杉醇正是人们一直在寻找的物质。人类没法模拟天然产物,这个是进化的结果。
紫杉醇的发现是人类药物发展史中的一次伟大发现,给人类治疗癌症带来了曙光,并启示人类发现更加有效的抗癌药物。尽管我是药物学毕业的学生,但是对这种时髦的东西不怎么感兴趣,不知道紫杉醇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很重要,能治疗癌症,但不知道它在药物研发历史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紫杉醇不仅是科学家打开生命大门的一把钥匙,而且还是医院治疗癌症的一线药物——肿瘤药目录表里第一个抗癌药就是紫杉醇。

当时世界各大公司、著名的研究室,都在纷纷竞争来实现这个分子的全合成。1992年我去美国,正好赶上这个末班车。当时很多实验室,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课题组,宣称他们即将完成紫杉醇全合成。我的导师当时介入该分子的全合成研究不久,因此,需要更多的人手参加此项工作。于是,他问我想成名吗,我说想,他说做这个就能成名,我说,好,谢谢。
六个月后,我奇迹般地将紫杉醇的模型做出来了。最终,我们经过近两年的日夜奋斗,完成了天然紫杉醇的首次人工全合成。这项工作轰动了世界,杨震这个名字也被很多人熟悉起来。好多人都说,这个杨震是过去沈阳药学院的那个杨震吗?是不是同名同姓的?当我做完紫杉醇的时候,有一天导师把我拉到办公室,说:“你不是一直想跟我照相吗?来吧!”
九死一生问苍天
紫杉醇将我变成举世瞩目的新星,1996年我又完成了抗癌药埃博霉素的首次全合成,1998年完成了抗神经毒素Brevetoxin A 的首次全合成。等我做完这三个复杂天然产物,我觉得我已经领悟了合成化学。那个时候“人类基因组”即将解密,当时“化学基因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哈佛大学的施莱伯(Schreiber)教授,讲人类基因组解密之后,两万多个基因如果能被有效调控,人类就不会有疾病的困扰了。当时我一听,觉得这才是我的梦想。
1994年做完紫杉醇后,我开始骄傲起来。好多次教会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一次我开玩笑说:“上帝,你就别挂在那儿啦,也不干活!下来干活吧,像我一样。”
不到半年,在一次实验过程中不幸发生了爆炸,当时我重度烧伤,达到30%以上,在医院昏迷了近两周。从医院出来之后,我全身的皮肤全移动了,因为30%的烧伤我需要植两次皮。第一次是拿下我身体30%的皮用来保护我身体被烧伤的部位,防止感染,而第二次植皮才用于治疗。
当时医生说我要截肢,我问截几个肢,他说可能截我的右手。我想了一下,说没有右手的话,有左手还可以活。后来有一天我的身体出现了感染,医生就说可能要截双肢。当时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没有双手的人该怎么生活,我说那我就不活了。然后医生说,这就看造化了。多亏我身体好,要是身体不好就活不下来了。
烧伤病人治疗上与一般的病人不同,烧伤病人不能输液,因为一输液就水肿。为了避免水肿,烧伤病人需要输高浓度的生理盐水,让你脱水。那个高浓度生理盐水的脱水过程真叫人难熬,我的嘴和舌头当时干得像锯锉一样。
起初的四周时间,我因为全麻醉移植后太痛,基本上都是在做梦,梦见在水里或者是在冰窖里,就是想喝水。我太太那时候天天给我拿纸蘸水点在嘴唇上。因为身体素质很好,到最后恢复过来,胳膊也没截。恢复期间他们也很佩服我,医生问我有什么梦想,我说我还想回实验室,他说我得配合他,因为我做实验要用我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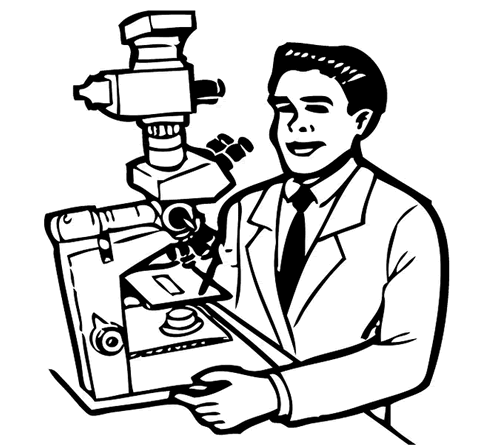
当我手背上的皮肤刚愈合时,他为了不让手背结痂,就用胶带把手掌和手指头缠成拳头状,缠到一定的时候他一使劲,把关节上所有的皮重新打破,血都喷了出来,整个纱布、胶带全是血。就这样,他让我手指的关节部位又复活了。
有个德国的女护士,我很感激她。她每次给我做处理的时候,把皮撕开之前她就先哭了,说:“你不是想回到实验室吗?求你忍住,对不起、对不起。”很多时候,我总是忙着安慰她,忘了一些痛。
当时胳膊是三度烧伤,胸和脸是二度烧伤,耳朵都烧没了,后来做了几次手术才得以恢复。很多人不相信我有这样的经历,我跟别人讲这个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好好编,我跟他们说这是我受过的磨难。
我当时出院后是不需要再工作了,因为我拿到了美国的终身残废保险。看完那封信之后我流泪了,当即就把信撕掉了。我儿子当时很小,才九岁,他说:“爸,那很多很多钱呢!”我当时跟他说:“不能要这个!你爸不仅不能靠别人养活,而且还要养活别人。”这对他后期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我儿子很刚强,很自立,我们根本就没有管过他,他自己成长得很好。他本科在康奈尔大学学生物,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脑神经生物学博士,现在在该校做博士后。他是很优秀的小伙子,他见证了我整个的过程,这是他生命的营养。
在这个九死一生的过程中,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提升,小时候的那些仇恨在这个过程当中全部被清洗掉了。

从那以后,我对生命有三个承诺。
第一个是不会再做坏事。我可以不做好事,但我绝不做坏事。我不能说我不犯错误,但我不会主动去犯错误,更不会报复、陷害、做偷抢之类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同情。我早期对吸毒人员很不尊重,看不起他们。我从医院出来之后,用了吗啡,但要戒掉吗啡的时候,那个痛苦很难控制。从那以后,我就对所有的吸毒人员有了重新的认识,他们是一群失落的人,不应该被歧视。我改变了很多这种以前的想法。
第三个就是尊重宗教。尽管出身不太好,但我一直努力向上。我学习好、听话,反正在学校里头,什么事情我都是努力去做。以前我对宗教是反对的,也没工夫去学,带有很大的偏见。从那以后我对宗教不评论,也不反对。
我在病床上痛不欲生的时候,医院里很多医护人员来探望我,他们以一种仰慕英雄的目光注视着我,表达他们的感激。因为我的导师告诉他们我是“合成紫杉醇抗癌药的英雄”。
许多个深夜痛彻心扉的时刻,我需要吗啡才可以挺过去。后来医生告诉我,对烧伤病人的伤害70%来自于病人精神上的痛苦,30%才是伤痛引起的,因此,病人的休息和睡眠很关键。带着这个信念,我积极配合治疗,努力睡觉,恢复得很快,半年后基本上不需要用纱布了。
后来这家医院里一旦遇到需要心理战的人,他们就去跟那些人说:“曾经有个博士很厉害啊,人家很坚强,配合医生的治疗,恢复就很快啊,人家已经又回到实验室工作了!什么叫博士啊,就是有梦想的人!”
我知道是医院里的药救了我的命。在医院里,当我痛得又蹦又跳时,一看到护士拿着装有吗啡的针,还没有给我打呢,我就开始安静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药是多么重要。
多少次我安静下来,内心都感慨这神奇的世界。上天啊,我该如何回报这救命之恩?忽然间我懂了,上天用这么艰难的方式,赋予了我一个伟大的梦想:去做药的研发,以此去回报这世界的救命之恩。

我立志做药,这个理念本身就是回报吧,选择做药救人,这是我生命的最高境界!于是,我选择了放弃眼前已经让我赫赫有名的领域,重新开始进入一个新领域,去哈佛组建自己的实验室,开展化学生物学研究,开发药物,拯救病痛中的人们。
离开哈佛,跟随林建华回家
到了哈佛,我成为哈佛大学医学院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率先开展了基于活性天然产物的结构多样性导向的组合合成研究。很快实验室就产生了一些抗癌和抗病毒药物的先导化合物。后来华尔街的投资人来找我,说我做得不错,大家很喜欢我,何大一(戴维何)愿意跟我一起开公司。我说好啊,但是我真对社会很不了解,我没钱。他说我不用投钱。我说那怎么合作公司。他说他们出钱,我做。我说做赢了,行,做输了,我拿什么赔?他说我不用赔。
我当时才意识到美国潜在的魅力,你可以靠能力去吸引资本。何大一听说我不错,各方面、人品都挺好的,然后他就说我们一块做公司吧。我就跟他在纽约创建了抗病毒药物研发公司,我也成为该公司的五位发起人之一。很幸运,我一直跟他干了八年多,我们俩很好。

到哈佛医学院工作是我生命中莫大的幸运。在那里,我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来从事科研工作,遇到了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生,见到了梦寐以求的科学大师并能亲耳聆听他们的演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渐渐感到孤独。当时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带给我许多无形的困惑和压力。我一直在想,一个民族不强大,你在哪儿都一样。我就跟尼克劳教授讲我现在很不开心。
2001年,时任北大化学院院长、现任北大校长的林建华校长请来访的尼克劳教授帮忙推荐做有机合成的年轻人回北大任职。尼克劳教授就推荐了我,他找我说:“你们中国的哈佛需要人,你愿意回去吗?”林建华校长也问我:“你愿意回来?”我说:“我愿意!”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吃了这么多苦,就这么待在美国,不甘心。”所以我回来了,义无反顾。
我早期回来的时候,我跟何大一的公司每年给我的北大实验室十万美金,整整七年,支持我们实验室运行。与何大一等人的接触教会了我爱惜人才。我早期在北大的一些学生一拿到美国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经常不在实验室工作了。为什么?他们说要去做家教,挣钱买机票,因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自农村。我知道之后就说你们不用再挣钱了,我给你们买机票的钱。因此,一些早期学生的机票都是我买的。人生很多时候就是缘分。
回国后每天追剧、跑步是我的娱乐活动。追剧是因为没过多的时间去接触现实社会,希望通过看电视剧来学习新语言、新概念,增强与学生沟通的能力。我也喜欢帝王片,最近又看了《康熙王朝》和《武则天》,希望通过电视剧了解历史。有趣的是在自己年龄的不同阶段,看这些史剧的感受也不同,常常发现对历史人物有全新的认识。《武则天》里面的一句歌词我很喜欢:“回头看是善是恶,还是千古的迷惑。”

回来之后我就到深圳建设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早期跟林建华一起戴着安全帽建校区,和吴云东院士、邓宏魁等一起开始了创业一样的生涯。我们建了一个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后来变成学院,现在又变成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步一步地推进。事实上这是筑梦的过程,也是必然的结果。
我尊重海闻,尊重吴云东,他们都是有梦的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我骨子里头也是天生的爱国主义者。
我很认同一句话——跟国家和民族一起爬坡。我当时觉得国家没钱,就像我们家很穷,但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回国参加建设,是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无比重要的责任,也是无上的荣光。
深圳真的很好,早晨醒来之后吃饭,然后就到办公室,中午太太就做好饭了,吃完了休息一会,一直工作到晚上七八点钟,然后回家吃饭。深圳给我一种很像加州的感觉,没有那种地域的文化,大家都很平等。从办事效率来看,深圳在中国是最好的,它没有官气,你能明显感觉到,官员是跟你同步的,真是跟你同甘苦,很多事情让人很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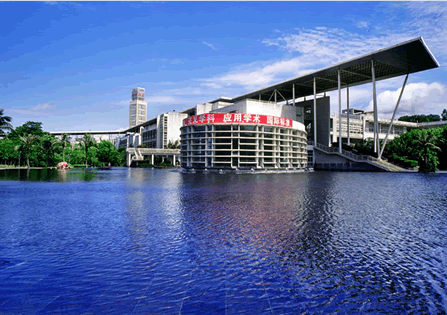
北大深圳是学者筑梦的地方。今天我们拥有了“省部共建肿瘤化学基因组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唯一从事基础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很感谢林建华、海闻和吴云东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梦想是做出中国第一原创新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老借助世界的文明来发展自己,中国要对人类做贡献。这个梦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因为做药事实上是一个建立在科学上的机遇,你就算再努力,有些时候你未必有这个幸运。做药的过程是个统计学,人多了,总会有人有好运。
好多人都说,你怎么每天都是这么激情满怀的?我就说因为周围的人让你不得不充满激情,他们给你永远品味不完的精神食粮。我要再提一下我的好朋友,也是早期创建我们新药研发平台的著名生物学家邓宏魁,他是个angel(天使),为科学而生,在自己世界里活着。我的人生很幸运,一路走来让我结识了许许多多值得为他们骄傲的人。事实上,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通过与这些杰出的人士结识,我的人生品位确实提高了很多很多。